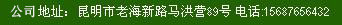|
那是年,我上大学三年级,暑假,我向系里申请了经费,元钱,考察京九铁路,调查京九铁路对山东的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影响。我从济南出发,北起临清,沿京九铁路线路一直到河南商丘,在齐鲁大地行走(确切地说,应该是鲁地),对所调查的当地的经济、文化、风情、民俗、历史等状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印象最深刻的是从临清到梁山一段行程。
“这里是季羡林的家乡。”站在连接山东与河北的一座小桥上,同学李君说,她指了指河的对岸,那就是河北的保定。在来临清之前,我就读过这位学贯中西,德艺双馨的学者的著作,知道他就是在这里出发,走向济南,考入清华,走向世界的,年,季先生出生的时候,当时的临清叫清平。我不知道在季先生眼中,临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我住宿的小旅馆里,河北人居多,在众多口音的交谈中,心中涌上来一种人在旅途的感觉。同学李君安顿好我的住宿,骑上一辆小巧的自行车,消失在临清的街道深处。我和同一房间的旅客交谈几句后,翻看起随身带的书,“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戴叔伦《除夕宿石头驿》)“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隔着遥远的时空,诗人的飘零感,不确定感,不安与寂寞,一下子击中了我,夜色下的小旅馆似乎总是笼罩着浪迹天涯的惆怅。为了排遣寂寞,我又翻阅起随身携带的关于临清的资料,追寻临清的前世今生。
临清是古运河的产物。京杭大运河是条长带,串起了沿河的城市珍珠。又何止城市,沿运河的一切存物,包括乡镇村庄,更包括聚居游走的人群,它曾经的往昔一直到可触摸的现在,都被划进可运河经济带,带有浓郁的运河文化色彩。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昔日的繁华,如今镶嵌在临清男女老少嘴上的一句老言古语。带有缅怀的意味,与其说是自恋,不如说失落。明清时期,临清是运河漕运的重要码头,“帆樯如林,百货山积”。临清是当时的交通要冲,“市肆绵亘数十里”,商业繁华的程度可见一斑。难怪乾隆皇帝写诗:“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据说,当年设在临清的税务所,是国家最大的税务所之一,税收曾经占到当时国税的七分之一。
在临清巨大的舍利宝塔下,运河是昔日繁荣的交通要道。我去的时候正值夏季汛期,河水丰盈,颜色浑浊,宽阔的河道由于有了水的滋润,河流顿时生动起来,用浩浩荡荡形容也许并不过分。我要考察的京九铁路飞跨两岸,像飞腾的钢铁巨龙,映着不远处高耸的古塔,古老与现代就这样组合在一起。我从河的一侧踏上了铁路桥,巨大的钢铁构架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炙热烫人,散发出钢铁特有腥味。河边有放羊的孩子,赤裸着上身,皮肤黝黑,更多的孩子们忍受不了阳光的烘烤,在河里洗澡。我猜想这是放了暑假的孩子,帮助家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李君说,他们中有不少根本就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也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贯通临清的京九铁路对他们的未来将发生什么影响。
在古运河边,仍然可以随处捡到古老的破瓷片,据资料表明是清雍正年间的沉船遗物。这些碎片提醒我,其实临清的荣耀和辉煌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金瓶梅》所写的地点是临清。在明朝的时候,临清“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是有名繁华的大码头。研究者认为金瓶使用的是齐鲁方言。在临清,听百姓说话,猛不丁冒出一句古典白话,让人感觉好象置身古典小说的场景中。对于喜欢阅读金瓶和水浒的人来说,仿佛隔着迢迢时空,在茫茫人海看到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令人惊喜,然而,更多的是慨叹。
历史绝对不是尘封在线装书中的资料,也不是静止的逝去的岁月,它仿佛是一条奔流的河,从遥远的时间、空间流到我们身边,以一种鲜活的面目出现。即使河流是干涸的,我们也能发现过去的痕迹。而一些东西很好地保留下来,比如一个地方的习惯、风俗、语言,即古老,而又风情万种。我们在一个地方使用的特有的方言中,可以感受的逝去的岁月是如何顽强地残存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同学李君的名字也曾让我感到奇怪,君作为一个女性的名字,似乎带有某种文化含义。我开玩笑地说,你的前生也许是明末的一代才女,也许就是《桃花扇》中的李香君。
作别李君,赶奔聊城。聊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江北第一水城”,最近,聊城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打出的就是这张牌,提高了城市的美誉度和知名度。的确,在聊城人的心目中,这个城市被水包围着,值得骄傲。我在光岳楼下停下脚步,这座四重檐的明代建筑,尽管没有岳阳楼的名气大,但它是聊城的标志性建筑。在光岳楼附近的其他古式建筑里,已经更换为政府机关。光岳楼就矗立在波光粼粼的东昌湖旁,一个是名胜古迹,一个是自然风光,给聊城增添了许多魅力。
让聊城人自豪的不仅仅是楼阁和湖泊,山陕会馆,海源阁藏书楼,曹植墓,《水浒传》里的种种遗迹,都可以看作聊城的精神资源,黄河,运河双双通过聊城的辖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在山东是落后的,在京九铁路没有开通前,聊城还没有火车站。和聊城人聊天,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发展的机遇。在尚未竣工的聊城火车站,一位开摩托车运送客人的中年汉子说,想贷款买一辆夏利跑出租,“大京九一开,聊城的客流、物流就海了,嘿,生意好得不得了,客人多得一刻也不得消停”。借着京九铁路的开通,聊城急于突围,突破封闭、落后的包围,树立一种新的城市形象。
在聊城短暂停留之后,我乘上由聊城开往荷泽的长途客车。和并排我坐在一起的是从荷泽火车站来的工作人员,他被调到聊城火车站,开始崭新的工作。和他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车已经驶出了阳谷,武松的故乡,一千年之前的景阳冈,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一千年过后,这里有火车驶过。阳谷,只是京九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世事沧桑,一个地名因一个人物,永远流传。我想象着此时的公共汽车就是即将飞奔的火车,我是一位旅客,我的下一站是梁山。这条路线让我感到神思飞扬,我的行程所在是《水浒传》、《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有《聊斋志异》中提到的地名,有《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颚踩过的足迹。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杂糅了学、文、商、侠、盗、妓的地方。儒学的仁义,江湖的侠义奇妙地融合。侠客走了、英雄来了;文人走了,诗人来了,皇帝巡视了,官员讲话了。娼妓和商人一起盛行,地痞和流氓一起流行。三教九流便构成社会,各色人等便构成了江湖。有社会就有等级贫富,有江湖便有恩怨情仇。
《金瓶梅》展现的是礼教的束缚走向崩溃,市民阶层的糜烂的生活,纵欲、堕落,贪婪,所谓的运河文化,原本就带有有钱阶层的享乐色彩。而《水浒传》中的好汉反抗朝廷强加给自身的命运,颠覆原有的生活秩序。梁山聚义,无非是儒学的仁与义,但无论怎样的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都掩住不内心的迷茫,很多人上山是盲目的,上山之后怎么办更加迷茫。好汉在节节胜利之后,又走上了招安之路,国家正统主义的观念是摆脱不了的。他们解除了被杀的厄运,只会杀人。很多人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仇视女人,特爱杀女人,其实和西门庆把女人当作淫乐的工具没什么两样。梁山好汉的下场都很悲惨,所谓英雄,一般而言,就是比一般人死得难看。
旅途无聊,想起这两部书,内心郁闷,倍感悲凉。
汽车进入东平,汽车在湖区行驶,湖堤上长满了高大了桑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这里是东平湖了,我猛然醒悟,离我的家乡汶上不远了。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骑自行车到湖里贩鱼的故事,我对这里充满了向往,没料到以这种方式途径东平湖,满足了小时侯的一个愿望。望着不远处的故乡,想起了唐人贾岛的一首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指并州是故乡。”(《渡桑干》)
此时,汽车抛锚了,司机骂骂咧咧地下车检查,乘客们乘机下车活动活动,我干脆跑到湖堤上,看看那些可爱的桑树。上大学,第一次出门远行,母亲送我出家门,在村南头的大桑树下,目送我走到兖梁公路。从次之后,在我眼中,桑树有了别离的意味,淡淡的伤感。我在湖堤的桑树下漫步,看到乘客向我招手,示意车修好了,尽快赶路。忽然想起一个典故,浮屠桑下不肯三宿,惟恐产生眷恋。原来,桑树催人上路啊。
黄昏渐渐逼近,太阳一点一点落在湖面上,柔和的光线布散在湖面上,一排错落有致的雨船停泊在湖边,东平湖让人感到纯净,自然,有一种未被污染的美。八百里的水泊只剩下这一片了。
向晚的风从田野漫过来,清清爽爽的,惬意的清凉,大地沉寂下去。车内的乘客也陶醉在柔美的黄昏里,沉默无语。
汽车进入梁山时,已经华灯初放了。水泊,梁山、武校的字样纷纷进入视线,就文学艺术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而言,《水浒传》更为广泛深刻,水浒影响梁山的不仅仅是旅游,而是渗透到各个层面的生活。我不知道京九铁路会在这里的小站停留几分钟。
这里离黄河近了,远处是黄河的呼吸…… 赞赏 长按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商丘市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召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